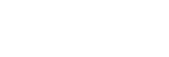《父亲的病读后感》
(一)
在《朝花夕拾》里读到了青年的鲁迅有份深藏不露的志气。《父亲的病》里写到,在父亲因庸医愚昧而去世后,为避开那无聊的流言,也为了母亲,鲁迅毅然到陌生的他乡求学。在日本留学时,为了救国图存,毅然谢绝了藤野先生的极力挽留,又放弃自己的专业,孤独地投入艰难的文艺运动------虽然这一切在文中都只是轻描淡写,但是蕴藏在字里行间的那股无形的爱国热情,把每一位读者的心都点燃了,这是在许多作家作品中都找不到的感觉。难怪一位日本学者说:“纵使日本有一千个川端康成,也比不上中国,因为中国有位鲁迅。”
人生阅历的疏密、时代氛围的错落,造就了不同时代不同人的思想。过多的“斗士”形象的渲染,让人过多的感受到鲁迅的“冷峻”,就像最常见的那尊他的胸像。当我们忘记鲁迅身上的光环,或者忘记鲁迅,细细品读《朝花夕拾》,就会发现一个“冷峻”外的鲁迅。从而发现鲁迅内心深处的一片净土。正是在这片净土上,散发着鲁迅许多人性的灵光,使他的文章洋溢出浓浓暖意。
父亲的病读后感(二)
文/李昂
鲁迅的童年之花虽然已凋谢,但在黄昏时仍能拾起来,在这里其中有一朵花,虽然不是姹紫嫣红,但它却让我感触颇深。这朵花就是《父亲的病》
文章回忆了儿时为父亲延医治病的情景,描述了几位“名医”的行医态度、作风、开方等种种表现,揭示了那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和草菅人命的实质。
由此,我联想到当时中国的落后,不仅仅是医学技术的低人一等,在思想观念上,综合国力上又何尝不是固步自封呢?正如曾国藩在《原才》中的两句诗“风俗之原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和“风俗之于人心也,始乎微而终不可御者也。”如果这两位“名医”就是《原才》中的“一,二人”那么中国更是难以走出落后的泥沼。
读后也暗暗佩服鲁迅的文笔,表面上冷静地叙述了事件的始末,却暗念着“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巧妙讽刺,如握一管如椽之笔,蘸那满腔心血,将守旧势力骂得入骨三分。正如郁达夫形容鲁迅的文字:“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之后,只消两言三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
这篇文章更是提醒我们,当下应刻苦学习,提升素养,不断进取发展,使我们伟大的民族摆脱愚昧,繁荣富强,这才是我们交的最好的一份读后感!
父亲的病读后感(三)
鲁迅下面这篇文章《父亲的病》,现在已经是很出名了。但是再出名,也无法改变当年他的遭遇。就象文章中所提及的“名医”一样,也并非名气大就可以起死回生的。读鲁迅这篇文章,我为其之痛苦遭遇而感到遗憾,如果其言属实,更是为这些装模作样、故弄玄虚的“名医”感到愤慨。
鲁迅当年家庭败落,其父周伯宜从监狱放归之后,变得喜怒无常、酗酒、吸***,脾气暴躁,脸色阴沉。先是咳嗽,然后是咳血,还合并全身水肿,最后严重到鼓胀发作,医治无效而亡,前后立时约三年。我们现在难以考证其父当年得的是什么病,不过从症状看来,初期有点象肺结核,后期就是明显的鼓胀。治疗类似肺结核的咳嗽、咳血,“名医”们往往是有法子的。但是要治疗鼓胀这种疑难病症,如果不是真正的大师,是很难做到的。
你还别说,生姜、竹叶、芦根、甘蔗这些东西对于清肺热去痰,治疗肺痈还是对证的。芦根始见于约汉末的《名医别录》,但是,这个药比较常用,应该在中药店里就有的,何至于要鲁迅到河边去掘,不解。倒是这“经霜三年的甘蔗”比较难得。竹叶、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都是些甘寒之物,虽然可以清肺热而泄火,但长期服用而过于寒凉是会败坏中气,令患者病情更加严重甚至死亡的,而且这些药也不是非此而病不能除的,能够替代之药多如牛毛,而且都是数千年长期筛选出来的,为何非要张罗这些当时也并不容易取得的药物呢?难道“名医”非得以此才能显示出自己用药之非同一般,医术神妙吗?
说实在话,诸如“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一窠的蟋蟀”、“平地木十株”这种以搜奇掠怪为能事,又让人难以备齐的用药法我是非常鄙视的,真正的大方之家是不会不考虑病患的疾苦的,真正的经典也是不会随便收录这种古怪的药引的。如果大家不信,可以去翻看经典的《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藏经》、《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是找不到这些东西的。这些东西的出现肯定是后世才有的。
“经霜三年的甘蔗”,大概是为了更寒凉些,因为甘蔗甘寒,入脾胃而泻热除烦,可清肺热,但患有胃寒、呕吐、便泄、咳嗽、痰多等症的病人不宜,会寒中下利,增湿起痰咳,经霜三年则更为寒凉,不但不容易找,而且于脾胃其弊端更甚。
至于蟋蟀,其性温,味辛咸,有毒,利尿,主利水肿、小便不通等症,是适合鲁迅父亲水肿病症的,但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要用原配的。文中说要用原配一窠,如果不是作者虚构污蔑,就是该“名医”太过迂腐。
平地木是可以药用的,但我学医半年来也看了不少医书,却从来没见过这味药,开始还以为是纳音,谁知道经过查找,才知道它是植物紫金牛,也叫叶下红、老不大,始载于什么《李氏草秘》的书,多长在山谷里的树阴下,象小矮樟,自然难找。性平,味辛、微苦。归肺、肝经。治疗新久咳嗽,痰中带血,黄疸,水肿,淋证,白带,经闭痛经,风湿痹痛,跌打损伤,睾丸肿痛。即使它有治疗水肿的功用,却肯定不是什么常用药。
如果就泄水利尿,消水肿而言,可以替代蟋蟀、平地木的良药太多了,《伤寒论》里到处都是,如茯苓、猪苓、泽泻、滑石、海藻、大戟、甘遂等,而且大都容易从中药店里得到,“名医”又何至于以此为难早已焦头烂额的病人家属呢?只有迂腐不化,无真才实学之医生,才会出如此刁难的手法,所以可恨!或者是患者历来专权跋扈,“名医”终于逮着机会故意为难一下,也未可知。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是真有水平的“名医”,非要用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以及平地木,都是无可厚非的,这是人家用药的特色而已,你如果不喜欢也可以有选择其他医生的自由,但是真有水平的“名医”绝对不会死板到要“原配一窠”的蟋蟀,所以,有人怀疑鲁迅这么写是夸张杜撰出来以污蔑中医形象,以泄个人私恨的,也未可知。
让人有点不解和可笑的是败鼓皮丸,败鼓皮是有记载可作为药用的,但是却用来治疗蛊毒,而非治疗鼓胀。说败鼓皮能破鼓胀,这属于庸医“意淫”的糟粕之流,是牵强附会的说法,是庸医无能的表现。鼓胀的根源黄师已经分析得非常精妙,可惜数百年来,少有人识。
梧桐叶可入药,若经运用合理,自然有验。但药引子的说法,其实也多是迂腐之医糊弄人的手段而已。看看《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等经典,从来没有药引子的说法。这都是后世之愚妄凭自己的臆想而无端生出来的。所以,鲁迅也说“医者,意也”,其实说得不好听点,甚至带有臆想、意淫的成分。能达到随意挥洒境界的大师毕竟是极少数的,就如书法一样,“书意”是很高的境界,不是简单的随便随意可以做到的。看似不经意很平常的寥寥几味药,就可以治疗痼疾或重病,玩味《伤寒论》里的首首经方,你才能感觉到医圣意境之高远,平淡之中见神奇。药有主药、副药之别,所谓君臣佐使,也不过是主次之分,虽然药有善于引入血分、气分、经络等之分别,但很多都是可以替代的,主要还是靠精选主药以及众药合力才能起效,大方之家是从来不说需要某个药引子才能治病的。愚蠢的人多悟不通这个浅显的道理,以药引子要挟病患,好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实在败坏之极。
事实上,心开窍于舌,所以说“舌乃心之灵苗”并没错,鲁迅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以为“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但是,光靠把丹点在舌头上,是无法治疗当时的重病鼓胀的,只能是糊弄人的把戏,连“名医”自己都没有底气了。于是连“名医”也怀疑起是否有“冤愆”来。
“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看看这句话,多少有点推卸责任了。如果你真能医病,那病就真该好了,痊愈后的病人第二天不小心掉进河里淹死了,那才叫不能医命。治不好病人,却还固执地说“能医病”,真要“能医病”,病人又怎么会日益严重而病死呢?这分明就是一个悖论。所以,推卸为“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至于“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鲁迅这么写,实际上是无意中抬高了这些所谓的“名医”,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怎么会是这样的水货呢?这绝对不是嫡派,见不到岐黄的真正影子,见不到扁鹊、淳于意的影子,也见不到医圣的任何影子,所见到的只有愚妄和迂腐,当然,人家是顶着“名医”的光环的,所以你很难追究和质疑。汉唐以后,这种非正统而曾经叫嚣、却也日渐没落之所谓医学,在经历数百年之流弊,杀人无算之后,终于又在日后成为大文豪的鲁迅身上发生了,所以才遭到鲁迅这位旗手日后有力的讽刺和挖苦,成为差点自取灭亡的代价之一。
巫医也许在早期是不分的,但随着中医的发展,它们彼此是分开的,而且可以区分得很清楚。医里有玄,但不是巫。扁鹊、仲景都是反对巫术的。扁鹊甚至说过信巫不信医者不治。仲景在妇人杂病里就明确说到“此皆带下,非有鬼神。”所以,鲁迅说的“也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只能说明鲁迅所见并非真正的中医大师,这或许才是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