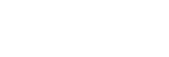《欲望乡野精选6篇》
欲望乡野范文 篇1
一张窄窄的车票,送我踏上回家的路途,火车一声长鸣,带着我向故乡奔跑,风驰而过的田野村庄,山山水水抛在了身后,熙熙攘攘的车厢里,花花绿绿的行包,张张满是兴奋的脸庞,唇齿一碰吐出天南地北的乡音,甜蜜和幸福,洒满了这一条长长的归乡路,这条路生长着思念,长满了牵挂。
故乡可好?爹娘可好,玩伴可好?那一方魂牵梦绕的山水可好?
端坐在一偶,静待故乡的临近,感叹这又是一年的漂泊生涯,像只蜗牛一样匍匐在别人的城市,为着生计不能停下疲惫的脚步,璀璨绚烂的城市街头,过往皆是陌生的背影,谁也不会在乎游子的来去。这高楼林立的城市,繁华之下有着太多的诱惑,为着这份诱惑,它不动声色的把汗水,心酸,委屈,茫然,孤独降临给你,让你受尽体肤之累,心志之苦。让你陷入这微醺之中,以为富贵垂手可得,以为流光闪烁的居所里可以栖下漂泊的身影,万家灯火中有一扇属于你的窗口。然而,现实何等残酷?在没有暖气的蜗居里一梦醒来,窗外冬雨丝丝,无情的将美梦淋湿。原来,这座城市的繁华终不属于你,你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罢了,可它又在某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为你点上一盏如豆的灯光,摇曳着微薄的希望,方使得你欲留不得,欲舍不能,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茫茫不知进退,唯有心中的故乡将心捂暖。
孤寂的心灵似乎对这种无奈早已妥协,对这种冷漠早已变得麻木,城市里的高楼遮住了望穿故乡的视线,夜幕之下,谁染一层白霜,铺在故乡的月梢上,照见我无处安放的乡愁?
风一吹过,乡愁就起,未曾启程,家已在心上。家门前那棵老树是不是落叶飘飘,片片夹带着思念飞舞在娘亲的秋水里?那渐渐老去的炊烟,是不是被爹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熏黄了季节的颜色?故乡还有放牛郎吗?那暮归的笛声,落在了哪一个黄昏中的野村?当初送我出门时的星星还挂在天上吗?我无数次留恋的那一片故乡的云,是否依然徘徊在蔚蓝的空中?
年货购齐了吧,腊肉一定熏得亮黄了,糍粑一定放在桌上了,烫面一定散发着青菜的芳香,挂在长长的竹竿上随风摇荡,小侄子一定又和他的小伙伴把炮竹零星的炸响,邻里街坊一定又在忙年了。秋叶落在大地,等待雪的掩埋,南雁执意北回,因为那是故乡,游子漂泊再远,剪不断一缕乡愁,那里天空蔚蓝,那里山清水秀,那里是宿命里改变不了的血缘,那里萦绕着亲切熟悉的乡音,那里挂着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美丽风景。
风尘仆仆的归乡路,尘封不住恒久的思念,思念太长,长过世上所有的路。出门前带着爹娘的千叮万咛,怀揣着希望和梦想,一年他乡的打拼,那份心酸不堪话语。是爹在远方时常的鼓励,娘在故乡捎来的温暖,让我孤单落寞中得以坚强,是希望和梦想,支撑着我在困境中奋勇前行。而今,一年过去了,虽不是衣锦还乡,却也背着一个充实的行囊,行囊里装满了孝心,思念和牵挂。需要爹娘来承受,需要乡情去化解,需要故土来听我倾诉。
欲望乡野范文 篇2
梁野山真静呀!静的能听清蓝天上飞翔的鸟儿那清脆的叫声。山脚下,清澈见底的泉水缓缓地流淌着,鱼儿在里面欢快地游,水面倒映出四周的苍翠树木,犹如一幅幅优美的风景画在流动。
梁野山真绿啊!满山长着郁郁葱葱、翠滴的树木,树木有高有低,站在高处向下望,山下那片树木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微风拂过,树叶一高一低好象是打起了一阵阵浪潮。红豆杉上挂着一个个红色的小果子,它挺立在群木之中,显得格外高贵,像高贵无比的皇后站立在人群之中。迎客松长在悬崖处,那棕色的树杆十分粗糙,伸出一双双长满青筋的老手正在热情地招呼前来游玩的游客们。松树的叶子像一只只小刺猬,坚硬的刺针依偎在树杆周围,那针状的叶子锋芒毕露,苍翠欲滴。特别是它们的松子,别提有多么惹人喜爱。高大的梧桐树有着粗大的树杆,上面有许多白色的黄色的斑点,树枝上的叶子像一个个巴掌,这儿一丛,那儿一簇,颜色有浓有淡,题目纵横交错着,看上去更威风了……
梁野山真高呀!从山脚向山顶望去,免不了一阵心惊肉跳。那高耸入云的山顶,笔直的石阶,险极了,爬在石阶上还担心自己会一不留神摔了下去。山顶插入云端,上面堆积着柳絮一般的白雪,人见人爱。雪白的云朵和雾气环绕在山的四周围,让人感受到人间仙境的滋味。
欲望乡野 篇3
关键词:都市视域 乡野文化 唯美倾向
对于马竹这个名字,熟悉湖北文坛的人想必都不会陌生。这个80年代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汉川人,以科班出身的文学根底、严谨治文的创作态度、30年笔耕不缀的写作实践,熔炼出了属于整体特征鲜明的艺术风格,即凭借独特的“都市旅人”身份对故土乡野的深情回望,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视域关照沉默而温柔的乡野大地。他的文字之躯在城市的森林里勃发,而他的根系和血液却来源于广袤的中国南方农村。
马竹的家乡是有着“鱼米之乡”美誉的江汉平原,别具一格的楚地水乡以富饶而润泽的水土温柔无声地滋养着世代依水而居的乡亲们。温暖的乡村生活体验连同他对美的最初认知、对水的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一起停留在马竹的记忆深处,这份对于故乡的眷恋与热爱贯穿于他的小说创作的始终,被贴上“豁湖”、“豁县”和“豁城”等地域标签,共同构筑起马竹诗意唯美纯净的文学理想国,不时散发出阵阵泥土清香。马竹长期往返于乡村与城市之间,在“农民的血脉、土地的儿子”和“现代都市知识分子”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之间不停地转换,使马竹不自觉地形成了两套笔墨,一套描绘都市,意图揪出都市生活“华美之袍下的虱”,揭示出物质挤压下都市人的凄惶与茫然。一套书写乡野,田园诗般美好的农村是永远说不完的乡愁,乡土情结和农村经验成了人精神上的救赎之门。两套笔墨相互照应,互为补充,凝结成了马竹的“乡村小说”和“城市小说”。
马竹擅写中篇,偏爱选用从农村走进城市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故事的第一叙述者,以生动贴切的主体代入性描述刻画当代知识分子的百态图,在众声喧哗中,触及都市男女千疮百孔的情感世界与爱无能的疲惫心态,当灵魂的漫步追赶不上物质文明大踏步前进的畸形发展,现代都市文化不断壮大的背后,精神上的一片荒芜就成为了必然,而马竹的笔端犹如章鱼触角上的吸盘,敏锐地挖掘出城市综合症候的根本病灶,还对症下药地开出了解毒的药方:回望乡野,从诗意盎然的乡野里汲取力量,找寻医治都市人精神之殇的灵药。从他的小说中不难发现,不论是《鸟语林》中的杂志社编辑孙援,《竹枝词》里的电视剧编导童济,以及《戒指印》中的作家袁明清,都同现实中的马竹有着如出一辙的文化背景。他们都以知识为手段改变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凭借着文采飞扬的才情从昔日的农村娃一跃成为都市的精英、城市的骄子,他们用贴心切己的温热体温呵护着都市跳动的脉搏,企图在漫长的余生里与整个城市水乳交融,不分彼此。然而外表浮华的都市生活并未给他们带来应有的身份认同与内心潜在的归属感。他们比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的进城务工者更敏锐地感受到都市市井文化中的人情冷暖,世道险恶。城乡文化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凸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得见的冷漠歧视和看不见的心理隔膜令他们即使在都市的物质给养中如鱼得水,精神上也犹如在边缘地带行走的流浪者一样形单影只,马竹在“城市小说”系列人物中塑造的最成功的莫过于《红尘三米》中的米家三兄妹,老大米福被父亲以“镰刀和斧头”的威慑逼进城市,却在都市里的滚滚红尘中踟蹰左右、进退两难:进一步,由于文化身份的暧昧不清,没有强有力的城市人际关系网支撑,他得不到认可与重用,甚至连朝夕相处的妻子都骂他“乡下狗”;退一步,他已无法再适应农村生活。反抗无门的最终结局是死亡,城市里最司空见惯的油漆桶竟成了夺走生命的凶器。面对城市摧枯拉朽的怪力,个人命运如蝼蚁般脆弱渺小,在广阔天地中找到心灵归宿的渴望如同玩笑,被弃如敝履,农村的故土反倒成了精神上的“望乡”,可望而不可及。与之形成反讽的是,米福的弟弟米根和妹妹米芝不顾一切的逃离农村进入城市,前一个租住商铺、与人姘居,靠贩卖盗版光碟为生;后一个在酒店做“妈咪”赚着肮脏的皮肉钱。两人的卑劣与麻木像镜子一样折射出米福的敏感与高洁,也折射出马竹对出走的年轻一代农村人中精神堕落者的深刻关切和无情鞭笞。繁华靡丽的都市霓虹使人沉醉,无数质朴的农村人为此丢下农具进入城市,迷茫而顺从地被物质文明剥离了身上流传千年的传统美德和高尚精神的外衣,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他们随波逐流,顺势而下,最终在欲望的漩涡中迷失了自我,异化成金钱的奴隶。在马竹的“城市小说”系列中,物欲的鬼魅时刻笼罩在都市的上空,都市不是人精神的栖息地和灵魂的安魂所,而是作为人生存的异质性因素永远存在的“异乡”。身处其中的人们找不到心灵的出口,只能逐渐被异质化的生活肢解得体无完肤,支离破碎。在对待生活时,他们疲于奔命,有的是紧紧抓住一切机会来垫高自己的地位,填充自己的荷包(《荒局》);有的是以不断逃离来抗拒命运之网(《红尘三米》);在对待感情时,他们心下茫然,试图以身体的短暂温暖慰藉空虚寂寞的精神世界(《一串红唇》、《空中有一颗桑葚树》);而坚持道德底线和个人尊严的少数“异类”被现实的车轮碾成齑粉(《北风吹》)。
作为都市异质文化对立面存在的乡野文化,原始自然、生机勃发、至情至性,充满了诗意涌动的唯美情调和质朴感人的精神内核,与人工雕琢、钻营算计、虚与委蛇的都市文化形成二元对立。站在现代都市视域下回望,犹如一幅神采飞扬、摇曳生姿的民间风情画。在小说《北风吹》中,“我”的老师王育18岁来到农村接受“锻炼”,这个城里姑娘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感受到了世间最温暖,最真挚的乡情,她不自觉的融入其间;而从小在乡间长大的喜文进入城市后却喜新厌旧的抛弃了王育。30年后,王育的女儿李丹正值母亲当年的花样年华,精神空虚的她试图引诱身为有妇之夫的“我”在公园里野合。马竹以母女的代际关系做了一个别有用心的巧妙对比,同样的年龄迥异的行为,母亲代表了乡野文化中美好的民族传统和伦理道德,女儿代表了都市物质对人的精神造成的毁灭性影响。马竹从不粉饰美化现实,不同于沈从文笔下浪漫气息大过于现实存在的湘西故土,马竹点破了中国当代南方农村面对都市文明的侵扰时产生的窘境,当传统的农耕文明被现代化进程的脚步踩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融洽关系遭到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也出现了裂缝。在小说《天下妯娌》中,作为二嫂的桃子渴望妯娌亲密无间,却不小心卷入了弟妹艳艳的家庭纠纷中,酿成了艳艳出走、桃子被打、婆婆卧床的可悲结局。故事中,纪家同辈里三兄弟中只有老二旺林与媳妇桃子一家在种田,老大媳妇翠翠在城里给富商做情妇,老三媳妇艳艳因为言行举止也被怀疑在城里有着不干净的过去。值得深思的是,马竹在此揭示了一种在当下农村越来越有市场的认识:农村女人要想在城里赚大钱就只有出卖自己的身体,但凡财产来源暧昧不清,或者举止娇媚的女人必定是做皮肉生意的。这种愚昧无知的劣根思想能够大行其道,说明都市文化的异质性对淳朴乡村文化的可怕腐蚀,也表现了马竹冷峻犀利的文化审视。故事最后桃子那句:“我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找到艳艳!”表现出马竹对于重建农村社会人与人互信互赖,温情脉脉的传统伦理道德关系的坚定信念。
马竹的文学审美是中国传统式的,他希望自己的文字“有着明显唯美主义倾向的美感传递”,因此充分利用传统诗词中丰富的古典意象,或直接以古诗词本身作为隐形脉络植入:在小说《荷花赋》中,乡村少女林瓷是马竹着力塑造的女性形象,小说开头以印日连天的碧荷红莲来暗喻林瓷的纯美洁净,以林瓷朗读王勃的《采莲曲》来暗示她情窦初开的少女情怀,在她得知父亲进京上访音信全无而感到孤单凄凉时,又以默写古诗《涉江采芙蓉》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安慰,可以说,“林瓷”这一形象融合了《边城》中翠翠式的娇憨天真和《红楼梦》中林黛玉式的多愁善感,因为来自广袤的农村土地,所以骨子里质朴多情;因为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所以脱离了盲目与愚昧。她是“美”的精灵,是“善”的化身,她代表了马竹对于“美”的全部认知和想象。在小说《竹枝词》中,以刘禹锡的《竹枝词》作为线索贯穿故事始终,首先是梁竹、梁枝两姐妹名字的由来即化用“竹”、“枝”二字,其次这首诗也是引发童济与梁枝思想交流的契机,对两人达成心灵上的相知与默契有着推波助澜的隐秘作用。马竹善于学习和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再加以萃取提炼,以诗意古朴的意象化语言勾勒出水墨画般的优美意境,传递一种“言之不尽、绵延不绝”的意蕴余味。
作为武汉作家的代表之一,马竹成功塑造了一批从农村走进城市,又因为文化身份的尴尬在精神上流离失所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反思都市现代性的问题上,马竹坚守着乡野文化积淀的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企图从面对乡野的深情回望中,实现人性冲淡宁静的审美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马竹无疑是成功的。
欲望乡野范文 篇4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3月26日生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高河镇查湾村,15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分配至中国敢法大学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海子在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他第一次用“海了”这个笔名发表的诗歌是《亚洲铜》代表作品有抒情短诗《亚洲钢》《以梦为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春天,十个海子》和长诗(太阳9系列等。海子在短暂的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二百多万字的诗作。
《春天,十个海子》是海子的最后一首诗作,它集中而透彻地履霹出诗人“本我”的精神追求与“异我”的世俗欲望之间的矛盾冲突,焦点化的展示出馋人从守望到绝望的生命过程。海子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诗歌家园,承受看来自那个裂变时代的各种变革浪潮的冲击。在这种坚守中,海子是孤独的。当他最后所理想的那片土地――乡村――也一如原始般的重复历史时,海子的理想之塔失去了最原始的根基,于是诗人选择了一种极端而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年,他才25岁。
在诗的第一节中,诗人劈头写到“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春天是一个生命勃发的季节,“十个海子”的复活,正象征着与海子的诗歌理想尖锐冲突的各种世俗欲望的复苏。这里的“十个海子”喻指自然的海子,它们象征着各种各样的世俗欲望,是与“本我”相背离的“异我”。它们“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你这么长久地沉睡究竟是为了什么?”这里的嘲笑也是诗人对自己心灵的拷问。为了傲“远方忠诚的儿子”,除了偶尔做做“物质的短暂情人”外,诗人把自己弓世俗的各种欲望割裂开来,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诗歌。海子的朋友西川回忆说:“海子在贫穷、单调与孤独之中写作,他既不会跳舞、游泳,也不会骑自行车。”海子自己也曾说过:“我有三种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但让海子感到迷惘的是,他的这种自我割裂并没有实现自己的诗歌理想,反而使自己与现实世界越离越远。于是,在这种痛苦的矛盾纠结中,诗人感到一种“影也把入抛却“的迷惘和困惑。
海子生活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靳的价值体系尚未确立。于是,一方面是惟利“务实”的世俗观念甚嚣尘上,一方面是作为艺术的诗歌备受冷落。于是在“春天”,世俗的“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着”,他们极为张扬,“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来蛊惑、挑衅精神的海子,进而“扯乱你的黑头发,骑上你飞奔而去,尘土飞扬”。我们可以想象到在这种对抗中诗人的基楚与坚守:他一方面承受来自物质世界各种欲望的挤压,一方面又始终不放弃自己的诗歌追求。海子不是两面神雅努斯,他不得不承受着“在大地弥漫“的“被劈开的疼痛”。
当世俗的“十个海子”“飞舞而去”只剩下“最后一个”“野蛮而复仇的海子”时,我们并没有看到诗人坚守后的兴奋,反而深深地体味到诗人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鲁迅在《自序》里说,“凡一个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而海子此刻正处于这样的境地里。于是诗人痛苦地写道,“这是黑夜的儿了,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在海子的诗里,有很多黑色的意象,“黑夜“、“黑头发”等。在海子的诗里,也常常流露出根强的死亡意识,如“我把天空还给天空/死亡是一种幸福”。我们可以想见,当崇高的诗歌理想被龌龊的世俗欲望无情冲击并玷污时,诗人在一呼无人应的境地里满眼潦黑,他着实感到一种生存的幻灭与悲哀。但诗人分明又是有省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眷念之情的,故而他虽“不能自拔”,但仍“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海子在乡村生活了十五年,他曾自认为,关于乡村他至少可以写作十五年。这个在精神上极端痛苦而孤独的诗人,寄希望于同乡村,麦子、土地的交谈来倾诉他的心灵隐秘,以固守他的最后一片净土。诗人充满热情地写道,“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子”,然丽乡村的因循守旧,那种最原始的状态又让海子感到迷茫。诗人在另一苜诗中也写过,“永远是这样/风后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前面是道路”。所以,当面对着“无视黑夜和黎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的“大风”时,诗人深刻地表白了自己内心的绝望: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曙光始终投有出现在他的乡村,尽管他一如既往地爱着乡村。据说,海子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始终处于痛苦焦灼的状态,一面是世俗欲望的纠缠,一面是诗歌理想的扳依。它们就像剪刀的双翼,海子无法将其统一在自己身上,所以当他割裂这二者的同时,也只能将自己的生命断然剪开。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子的死不是他的错,而是那个时代使然。纵观海子的《春天,十个海子》,我们分明听到一个凑苦的灵魂在饮泣,在呼告、海子死的时候,身边带着《圣经》和其他几本书。《圣经》上说,“生前所不能实现的,死后一定会如你所愿”。我想,那长长的铁轨也许就是一道天梯,定会将他送到诗歌的天堂的。我衷心祈祷着。
附海子的《春天,十个海子》
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
在光明的景色中
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你这么长久地沉睡究竟是为了什么?
春天,十个海子低低地怒吼
围着你和我眺舞,唱歌
扯乱你的黑头发,骑上你飞奔而去,尘土飞扬
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
在春天,野蛮而复仇的海子
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
这是黑夜的儿子,沉浸子冬天,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
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子
它们一半用于一寡六口人的嘴,吃和胃
一半用于农业,它们自己繁殖
大风从东畋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
欲望乡野范文 篇5
春天,田野里万物复苏。小草慢慢地从肥沃的土里钻出头来,探头探脑的;迎春花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有的花瓣全展开了,露出了黄灿灿的花蕾,有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鼓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笔直的大树上,吐出了嫩黄色的柳絮。青的草、绿的叶、各色鲜艳的花,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光彩夺目的春天。
小燕子从南方赶来,为春天增添了许多生机。几对燕子飞倦了,落在电线上,蓝蓝的天空下,从远处望去这几痕细线多么像五线谱啊!停着的燕子成了音符,谱成了一曲春天的赞歌。
夏天,太阳烘烤着田野。西瓜地里结出了许多又大又圆的西瓜;门前高大的树上长满了叶子,密密麻麻的,遮住了火辣的太阳,可凉快了。
秋天的田野真是个五彩缤纷的世界。瓦蓝瓦蓝的天空中飘着洁白的云朵,秋天凉爽的风吹来,给人神清气爽的感觉。各种各样的果实挂满枝头,在秋风中飘摇舞蹈。看,那红艳艳一片的是什么?原来是红石榴,鲜红欲滴的,真是诱人;那黄澄澄的一片是熟透了的橘子,一个个沉甸甸的橘子压弯了枝头。农民伯伯正在池塘里忙着挖藕,他们顾不得脸上、身上的泥巴,只见他们热火朝天地埋头苦干。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出汗了就挥起袖子一擦。我想,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是因为他们正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我被这场面深深感动了。
欲望乡野范文 篇6
关键词:荒野 生存 意义流失
哲学家萨特认为,人在世间的存在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苦难历程。在作家刘恒的笔下,生存的苦难也是无处不在。刘恒用犀利而冷静的笔触,通过平淡的日常生活故事、琐碎的细节,勾勒着人困窘的生存画面,向世人展示着芸芸众生的艰辛生存本相,让我们直面生活的真实与残酷。
一、本能欲望的展示
欲望对人性有着深刻的影响,它是“人类感性生命需求的一种表现状态。”不仅有其自然属性,也有其明显的社会属性。因此,在刘恒的“洪水峪系列”的乡村荒野的世界里,本能的欲望无论遭受压抑,还是被彰显,不仅外在地表现了社会时代的风云变革,而且内在地勾勒出人类的精神动向。
古语讲:民以食为天。粮食自然也就成了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需求和必然条件。在物质匮乏的乡村荒野世界里,吃是个永恒的主题。
《粮食》中,女主人公瘿袋为了粮食被卖了六次,为了让家人填饱肚子,不再忍受饥饿的折磨,她放下做人的尊严,千方百计的寻找粮食:煮树叶,掏鼠洞,淘骡粪。在历史的长河中,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饥饿本身就成为考验人们存活的残酷方式,它遮蔽了人的尊严和价值,让人失去起码的礼仪廉耻,人们认为只要活着就是幸福。当我们理解这一切,再回头看看瘿袋一家津津有味地吃着骡粪中淘出来的粮食时,便不会觉得触目惊心、不可思议。因为刘恒就是要向我们展示震撼人心灵的图景:在物质极度匮乏的乡村荒野世界中,人们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地活着,在“食”这个欲望的支配下,其他事情都显得无足轻重。
刘恒以“食”这个最基本的生存本能向我们展示了乡村荒野中人的生存状态,告诉我们这是粮食的极度匮乏导致的生命弱化的悲哀。
与“食”一样,“性”也是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刘恒对于“性”观点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不回避对“性”的书写,而是对“性”有着直面、正视的姿态。《伏羲伏羲》是反对性压抑的,但刘恒不认为解除性压抑会让人生命力勃发,相反会让人走进性的困境。与《粮食》中的瘿袋一样,《伏羲伏羲》中的王菊豆也是小地主杨金山用二十亩地买回来的媳妇。在婚后不久,却与家里的年轻后生杨天青相爱。两个渴望爱的年轻人有悖伦理道德的规约,偷吃了禁果,也将自己推进荒野的黑洞里。
刘恒把人的精神深层的东西,毫不保留地、直白地剖示给我们:在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下生存的乡下人,实际上一直被这种旧文化所控制,他们一直生存在这个自闭得无法自救的乡村荒野的世界里。
二、几乎无事的悲剧
在刘恒的笔下,偏僻、闭塞、固陋是“乡村荒野根本性的生活形态。”在刘恒极度贫困的乡村荒野世界里,出现了一批拜倒在财富脚下的人。因为物质的匮乏,他们不惜争夺财富互相斗争,最终成为财富的奴隶。比如:《狼窝》中的史大笨,为了煤窑能挖出煤来,不顾劳作的繁重和性命的安危;《龙戏》中的张广仁,因为煤窑被村里收回,财富被村民均分,愚蠢地想要炸掉煤窑;《陡坡》中的田二道二以洒满钉子和钢屑来扎破别人的车胎以求发家致富。
在这个世界上,财富和权利最能改变人的本性。为了金钱和权力,人们不择手段地相互斗争,甚至迷失自我。刘恒以冷漠的态度勘探人的生存本相,他当然不会放弃权力对人的异化的书写和权力对人性挤压的生存状况的考察。于是,刘恒又在乡村荒野景观中向我们展现权力对人性的破坏,将人性本善驱赶到恶之门的悲剧故事。
在“洪水峪系列”小说中,《两块心》是刘恒较早的涉及权力话题的短篇小说。它叙述了主人公乔文政从一个憨厚朴实的农民到最后成为服装厂厂长的经历。小说故事情节看似简单,但个中反映出的思想内涵却耐人寻味。《萝卜套》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农民的权力观,当他们被压迫时,希望反抗,当他们有权力时,又常常迷醉于这种权力。窑梆子柳良在窑主韩德培从烽火筒的老崖上摔下来变成之后,摇身一变成为另一个“韩德培”。
财富和权力虽然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命运,但也给人的精神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和创伤。所以,刘恒对财富和权利的描写,没有从其正面的角度去描述,他竭力想要表达的是人们对财富和权利的追求给他们带来的各种悲剧,人们对财富和权利的追求不是幸福的开始,而是灾难的肇端。刘恒以复杂的感情,裸地展现了在乡村荒野的温床上人性恶的滋生。
三、生存之重的追问
在刘恒的作品中,饱含着深刻的人性化哲思。“洪水峪系列”以罕见的激情描绘了人的生存窘状、人性的丑恶与善良、理想的破灭与绝望、现实的残酷与温情等。
无论刘恒叙写什么,他都是想通过最基本的人性视角,以文本为载体,向我们展现在极端贫困的物质生活中人们的生存状态。他冷酷无情地将“洪水峪”农民的所有生存本相一览无遗地展现给世人,让人惊叹。不管人们内心如何怀疑,如何抗拒排斥这让人震撼的生活画面,刘恒始终冷静残忍地告诉你: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你无所逃避。《粮食》中,刘恒采用原生态的书写,不掺杂任何情感与美感,叙述人们因为吃食放弃尊严;《狼窝》讲述了史家父子承包煤窑,急于摆脱贫困落后的生活,不惜牺牲性命而拼死的劳作。
在刘恒的“洪水峪系列”中,他翻来覆去地讲述关于洪水峪农民的故事,无论从“食”“性”“力气”,还是从财富和权力等这些不同的角度,他都给自己笔下的人物不断地设置生存困境,将人的生命本能和承载人生命本能的日常生活推向永恒的悲惨境地,以此来呼唤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和富有拼搏奋斗精神的真正的人的回归。
参考文献:
[1]叶君。乡土・农村・家园・荒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王斌,刘恒:一个诡秘的视角[J].文学自由谈,1989,(1).
[3]郑朝阳。试探人的终极关怀的真谛[J].学术研究,2001,(12).
[4]陈炎。国人的生存困境――刘恒小说三题议[J].理论与创作,19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