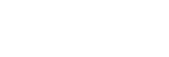《韩寒作品集(优秀3篇)》
小镇生活 篇1
这是我在小镇呆的第四天,书的腹稿已经打好,只差搬出来写在纸上了。
不过小镇的宾馆实在太吵,外面天天施工到半夜。
服务台说,这就是小镇在日益发展的象征。
我有点生气地说,你们宾馆扩建至少要保证客人的休息吧。
你别以为门口挂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人家就当你是五星级的宾馆。
服务生有点忍不住了,说你要安静就去古镇区租间房子。
她的话刺激了我。
我收拾好行李,和这家宾馆匆匆而别。
小镇非常古老,分两个镇区。
古镇区的明清建筑保留完好,政府正要开发这里。
游人尚不如织的原因是,小镇一来名气还不响,二来没有过哪个名声显赫的人物在明清两朝里住过这里,缺少名人故居,所以对一些没有文化的游人来说这里缺少了一种文化底蕴。
政府常抱怨明清的文人没眼光,只知道人多力量大,成群结队往周庄跑。
我经过小镇的柳永弄。
弄名是政府给起的,原来叫万福弄。
永远的远方 篇2
“远方”这个概念是相对的,现实的人往往把相对于自己的居所而言的另一个城市称为远方。
于是,我们看多了诸如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的小说,那叫逃向远方,管他两个城市相距多远,哪怕坐火车过去票价都超不过五块钱。
我一向认为,这些人没有远方概念,就算是上趟厕所也够去一回远方。
另一种人是不现实的,从南沙群岛到漠河不能算去远方,但从漠河到赤塔就算去一趟远方了。
这类人的远方概念是以国家而论的,在国境线上跳一个来回就算是打远方回来了。
我认为,远方应该是距离上的。
这个认为很废话。
距离很能吸引人。
别以为只有诗人歌手才会去远方流浪,其实每个人都向往远方。
惟一不同的是,有的人只向往而不往,有的人向往而往。
在今天的《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关于远方的文章,写得并不怎么样,文笔软得像块水豆腐,文章散得像碗豆腐花。
但就是这篇小豆腐块,让我有了写篇大豆腐块的欲望。
我向来很欣赏那些背起背包去远方的人。
今年第2期的《视野》摘了《现代女报》上的一篇《野鸭与IBM》,看了颇有感触。
IBM的创始人华特生的儿子小华特生,常常给员工讲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酷爱自然的人每年秋天都要去看野鸭南飞的景观。
有一年,他大发慈悲,带了一大袋饲料,到那里的池塘边去喂养野鸭子。
过了几天,有些野鸭贪吃不再大老远地南飞了。
三四年后,它们长得肥肥的,再也飞不起来了。
讲完这个故事,小华特生说,人们很容易驯服野鸭,让它们哪里都去不成,但要把它们再驯养成野鸭就困难了。
小华特生把这个故事翻来覆去地在公司里讲,他希望员工能理会其中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
有一次,一位员工对小华特生说:先生,你不要忘了,野鸭也是列成方阵飞的。
小华特生说:当然,野鸭也是有约束力的,得朝一个方向飞。
这也许是IBM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坦白说,这篇小文字是失败的,由野鸭而得到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牵强得一塌糊涂,莫名其妙。
但是,野鸭的故事却很有意义。
许多看似一天到晚去远方的人,其实是缺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不过,文中有句话算是说对了:“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
一个人如果活得像块方糖一样呆板方正,那么他的价值还没有一块方糖大,方糖可以让水变甜而他不能,更何况方糖还有棱角而他没有。
荒唐。
前些日子在网上读到苏童的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路上》。
这是近一年来惟一一篇让我读了两遍的小说。
回来后,一直跟斜上铺的“蚊子”说起,说得“蚊子”春心荡漾。
“蚊子”挺喜欢雪,所以追问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要多少钱。
我问他要坐的还是卧的,坐的便宜,卧的贵。
“蚊子”挑了硬座,我说那便宜,两百块钱不到,只不过从上海坐到吉林恐怕已成冰雕了。
于是“蚊子”挑了卧的,开始选硬卧,但望字生义,以为硬卧就像农村死了人躺在门板上一样,又改选软卧。
可一打听价钱,知道自己是有去无回,便挥挥手说:“算了,不去了,等工作了再说。
”我知道等“蚊子”工作了以后定会诸事烦身,再为自己找理由推托。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想去远方的人去不了远方的原因。
但去不了也好,可以让远方永远在心里保持神秘感。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想去远方的原因。
个人 篇3
我1982年出生在一个小村庄。
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是那里的广阔天地造就了我以后一向的无拘无束。
现在想想小时候真的很开心,夏天钓龙虾,冬天打雪仗。
但人不会永远留在童年,6岁那年我去镇上念小学。
小学的我,品学兼优,还当过三好学生。
那时起,我开始读课外书,嗜书如命。
一到晚上,我就窝在被子里看书,常常看到半夜,真是佩服自己的这双眼睛百看不坏,视力向来绝佳。
只是父母不允,常常在我看得紧张之时杀过来,没收书,逼我睡觉。
我只好待他们睡着以后再拧亮台灯看。
我无书不看,只是有一个怪癖,唯中外名著不读。
那时我就觉得好些特被人推崇的长篇小说文笔拖沓,太强调思想性,而且有的翻译得半生不熟,读了几本后就觉得是浪费时间。
直到现在,我还没读全过一本外国名著。
另外就是不看作文辅导书,因为辅导书里例文无不千篇一律,陈词滥调,虚编乱造。
只是当时学校规定非要买,我也只好买了,那些书后来都被我折纸飞机了。
小学里,我的文章并不突出,原因很简单——偏题。
往往写一半就不知偏到哪里去了,而且试卷上的格子不够我发挥,常常才开了个头就只剩下四五个格子了。
初中是我的转折。
我在初中转到县城一所不错的学校,语文老师是副校长,一看我的第一篇作文《我》就赞不绝口,直夸我奇才。
但问题同时出现,我的理科渐渐不支。
偏偏我进的班级是特色班,第一次考试三门课我考了273分,平均91分一门,不错了。
我估计应该在班级前五名,结果一看成绩单愣掉,42名,能倒着数了。
后来我开始投稿,投稿的动机说来可笑,只因为暂时缺钱。
一个礼拜里写了十几篇小说、散文,没打草稿,没留底稿,寄给了江苏、上海的两家《少年文艺》以及《少男少女》、《当代学生》,以为我今天寄去,过个把礼拜就会有稿费寄过来。
最先等到的是江苏《少年文艺》饶雪漫老师的信,鼓励我说小说写得很好,决定发表。
所以可以说,我的文学之路是从《少年文艺》开始的,而且《少年文艺》最令我敬佩的地方就是尊重原作,很少删改,保留原汁原味。
几个月后,我看到《少男少女》上一篇文章写得不错,挺像我的风格,想看看作者大名,不料一看名字两眼一坠,那篇文章竟是我写的。
删改情况可见一斑。
《傻子》发表后,我很高兴,去外面吃了一顿自我祝贺。
两个月后,发表了一篇《书店》。
我们班主任是数学老师,看了我的文章觉得恶心,因为我一向不喜欢“啊”个不停地去赞扬谁,然后结尾表决心要向他学习。
班主任说我文笔下流。
我气得宣布,今后一百年里,我们初中没有一篇文章可以超过我韩某人。
我厌恶那做人的所谓真谛——“圆滑一生,虚伪是真,四面讨好,八方奉承”。
别人夸你你要说自己不好,明明别人不好也要赞扬“你比我好”。
加上我生性不爱受困,常常违反班规,班主任常罚我抄班规20遍,我只好三支笔一起握。
我常对人说,我的一手好字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一次长跑比赛,一向长跑不及格的我被逼去跑。
由于前一天莫名其妙被罚站了四节课,站得我脚无知觉,竟一路领先,捧得冠军。
全校诧异。
以后的每届长跑比赛,我都稳获第一,区里也不例外。
其实,自己的潜力你往往不知道,要靠自己去发掘。
中考前我拼命补理科,上海中考规定语数外每门120分,我数学竟得了115分,吃惊不小。
更令我吃惊的是,语文94分,查卷下来,大作文被扣去十几分,大概因为我没写光明面。
幸亏我的长跑成绩1500米跑进5分钟(上海人普遍跑得比较慢),作为体育特招生进了市重点高中——松江二中。
进了松江二中要住校,无父母管教,很幸福。
我每天上课看书,下课看书,图书馆的书更是被我扫荡干净,只好央求老师为我开放资料库。
中午边啃面包,边看“二十四史”。
为避免我的文风和别人一样,我几乎不看别人的文艺类文章,没事捧一本字典或词典读。
看了书后,我却懒得写。
我最恨人家看了一本书就像母鸡下蛋,炫耀不止。
我美其名曰自己乃是多看少写。
我的性格里叛逆的因子太多,所以我的文章从来都有攻击性。
松江二中里几位资深的语文老师都被我笔伐过。
我喜欢在各种书里找错误,甚至教材里也被我找出不少。
同学们常看我的周记,说:“韩寒,骂得好!骂出了我们的心声!”我觉得这句话很可笑,既然如此,你们怎么不敢指出?这世上正义的人比比皆是,为什么报道里有那么多的见死不救?这些都源于人性里的懦弱怕事。
一进松江二中,我很好奇,广播站、合唱团、文学社、校刊编辑组都参加了,后来一个一个退出,因为这些都很花时间,况且会议不断。
我痛恨套话,开个会要感谢半天,感谢好后检讨半天,真正的内容大家会后讨论!真是佩服他们,从一局象棋比赛里可以看出科教兴国、爱国传统;一篇缺乏创见的小论文里可以反映出改革开放20年之成就……我自命博古通今,联想却不及他们发达,自叹不如,水平有限,还是退出来再安安心心读些书比较好。
我觉得文章如何写好写坏不见得是作文课上听出来的,而常常是从各种书上看来的,水到渠成,看多了自然下笔如有神,而不至于一篇文章写好,笔已经被咬得不像样子。
名师未必出高徒。
这里有一个矛盾:真理往往是在少数人手里,而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到头来真理还是在多数人手里,人云亦云就是这样堆积起来的。
第一个人说一番话,被第二个人听见,和他一起说,此时第三个人反对,而第四个人一看,一边有两个人而一边只有一个人,便跟着那两个人一起说。
可见人多口杂的那一方不一定都有自己的想法,许多是冲着那里人多去的。
我是那第三个人。
虽然可能讨人厌,但我始终坚守我的风格。
我不够谦虚,老师常说我不尊重人,笔无遮拦,品德等级顶多“良”。
我不在乎这个,一个人的品德根本不是优良中差能概括的',常有人劝我:“你太直话直说了,不会做人啊!”——看,人多力量太大了,连“做人”的概念都能扭曲。
我只是照我的路走下去,偶尔也会被迫补理科,力求及格。
我感谢两个人:一是我自己,读许多书;二是我父亲,允许我读许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