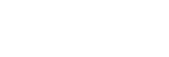《道士塔原文【优秀2篇】》
《道士塔》是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一篇散文。这次为您整理了道士塔原文【优秀2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并分享出去。
道士塔赏析 篇1
《道士塔》和《莫高窟》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如果说前者提示了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之悲剧,那么,后者则是对这一灿烂文化的赞叹和歌颂。两篇文章归结到一个主题: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这种文明是如此博大而辉煌,又是如此命运多舛。它历尽沧桑,迄今仍然生生不息。两篇文章是作者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反思,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
《道士塔》全文四个部分。作者融记叙、议论、抒情于一体,展示了近代中国由于愚昧和落后而带来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作者有“道士塔”作题目,寓意深刻。这座道士塔既是民族耻辱的象征,又是近代中国文明衰弱的标志。它是曾经发生过的、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
第一部分记叙了外国冒险家疯狂地掠夺和俞劫数以万计的敦煌文物。作者的感情表面上是平静的,但平静中已涌动着无法遏目的悲愤。
第二部分点出敦煌文物被毁被盗的原因之一:愚昧和无知。劈头就是一段议论,悲愤之情跃然纸上。接着叙述王道士破坏敦煌文物的罪恶行径,无奈中兼有揶揄。最后一个自然段,是作者悲痛之情的迸发,这是一种出于对祖国灿烂文化的热爱的神圣之情。
第三部分揭示了造成敦煌国宝大量流失的根本原因:旧中国的落后和腐败。作者用凿凿有据的事实告诉人们:我们必须正视这场中国近代史上的浩劫和悲剧,唯有正视历史,才能反思。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作者的悲愤、无奈之情。
第四部分写这场悲剧的终结。历史已翻过新的一页。大量的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止是民族的屈辱,也给专家们研究华夏文明史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但是,中华民族毕竟站起来了,令人欣慰的是:敦煌的辉煌仍然在中国,敦煌学仍然在中国。比之前三部分,这一部分虽然简短,但作者的思想感情又是复杂的,压抑、悲痛和自豪的心情交织在一起。“道士塔”作为民族文明的耻辱和衰败的象征虽然成为历史,但它足以警策每一个中国人:决不能重蹈覆辙。
道士塔原文 篇2
(选自2002年01月版《文化苦旅》)
一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
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
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
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
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
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1],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家投来羡慕的眼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
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
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
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
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
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雕塑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柔的浅笑有点尴尬。
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雕塑委曲一下。
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
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
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他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迷惑不解。
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三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呵,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以前,他正衔着旱烟管,扒在洞窟里随手翻检。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是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专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付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王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了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王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账,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5大箱、600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估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于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了王道士的圆寂塔前。